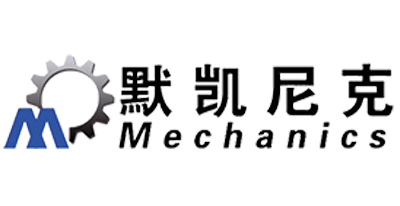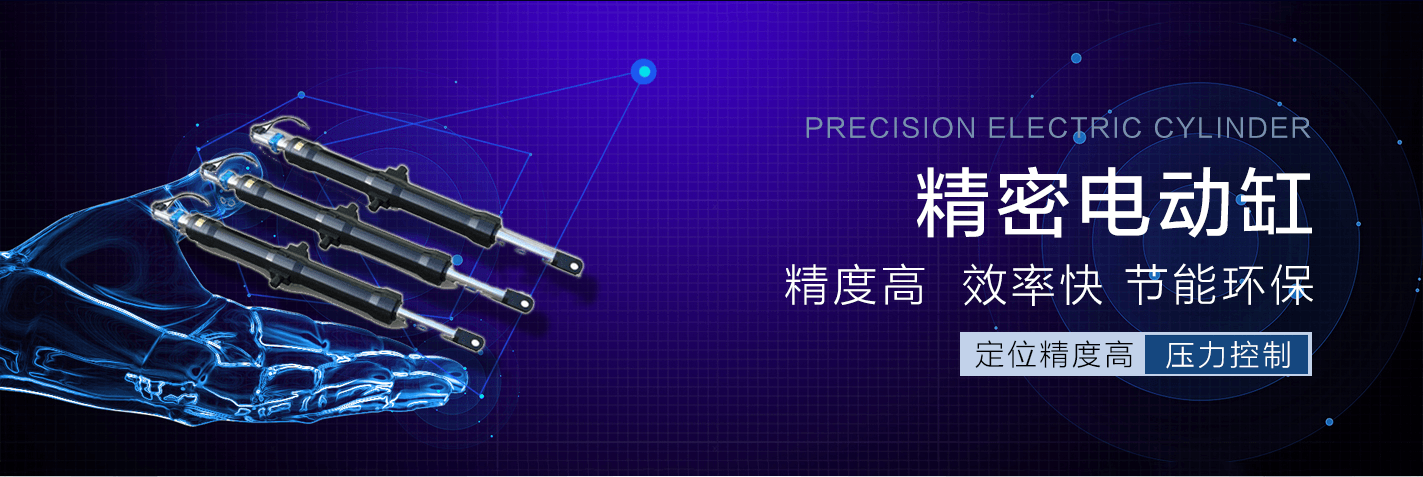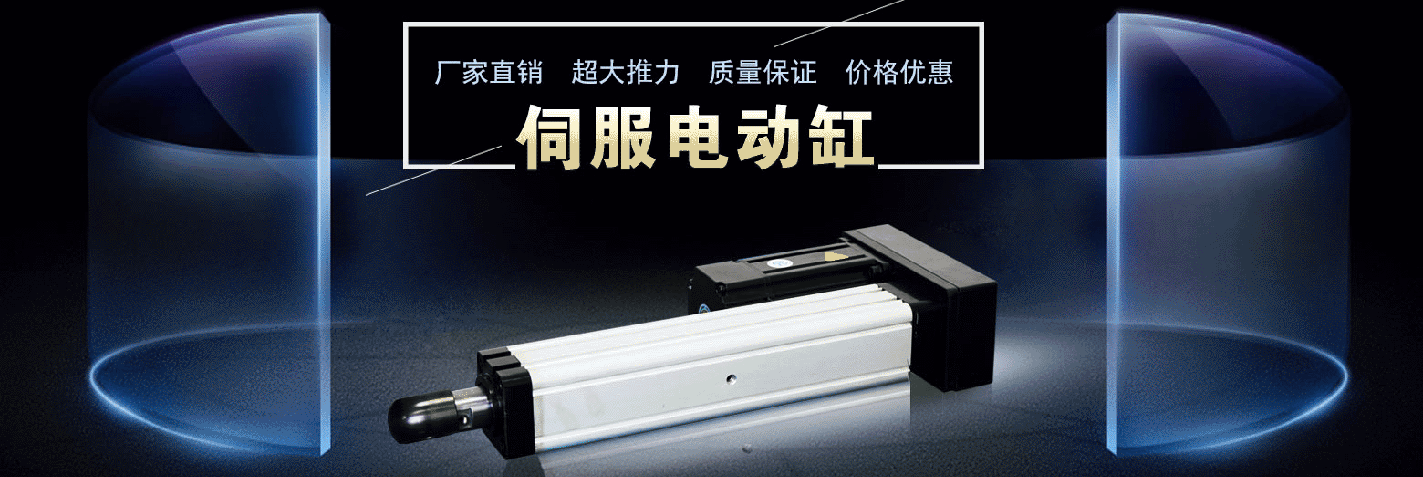红岩春秋(84)
来源:ca8888 发布时间:2025-06-25 17:11:55

合川县金子乡是地下党长期扎根经营的一个据点。陈伯纯回乡后建立了“两面政权”,1945年党组织又先后派来刘石泉等,“刘石泉以乡公所师爷身份在街上与三教九流接触,进行活动。他能力强,工作方法也多,很快就把局面打开了。”(《川东地下党的斗争》陈伯纯“我所参加的华蓥山武装斗争”)1948年2月,陈伯纯被敌人怀疑,转移到广安。
8月22日,王璞、罗永晔、罗纯一到金子乡,召集紧急会议,部署发动起义。陈伯纯在广安参加观阁起义后,也赶回合川,参加领导金子乡起义。会议决定8月25日在合川金子及邻近的武胜真静同时起义,由陈伯纯担任四支队司令员,王璞兼政委,下设三个中队:一中队由王子云、秦鼎负责,二中队由张伦、陈自强负责,三中队由楼阅强、符其燮负责。23至24日,各中队收缴地主和各保子弹,进行战斗准备。由罗永晔草拟,王璞修改的“起义军布告”,内容是“我们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是领导的队伍,是为解放受苦受压迫的人民而战斗,目的是消灭反动派,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希望一切军政人员立即觉醒,弃暗投明。否则,将受到人民的惩罚,没有好下场!”末尾署名:“第四支队司令员陈伯纯”。
8月25日是真静乡赶场的日子,街上人来人往,十分热闹。秦鼎带上十多个身藏短枪的战士冲上乡公所办公楼,正在吃饭的乡丁还未回过神来便被全部缴了械。这时在茶馆打牌的副乡长李绍清见街上有人来回奔跑,跨出茶馆,挥手叫喊:“出啥子事了?”秦鼎冲过去几步,举枪对着李绍清胸口,缴了他的手枪。游击队员还扯下乡公所的党旗,剪断电话线,砸烂乡公所的牌子,插上游击队的旗帜。
张伦带领政工人员在街上贴标语,散传单,还开仓放粮。旗开得胜的游击队,打下真静乡后,喜气洋洋向合川金子乡挺进。
张伦、陈自强、王子荣等带领的队伍也分别到了金子乡公所,汇合后进乡公所提枪。金子乡陈伯纯的继任乡长陈缉熙是一位统战对象,乡丁枪弹也多控制在游击队员手里,张伦带队伍攻打金子乡公所其实是故意制造的假象,陈缉熙和乡丁在乡公所朝天放了几枪,随后便参加了起义军。
攻下金子后,游击队开仓济贫,搬出乡公所的文书档案和蒋介石挂像,党旗当众烧毁,许多农会会员、青年手执梭镖、大刀要求参加游击队,队伍竟壮大到一千余人。
8月26日上午,经过整编的约四百余人的队伍到了真静乡黎家花园附近,一面准备午饭,一面派人去收缴附近地主的三十余支。武胜县中心镇镇长康良带一百多人企图堵截游击队。陈伯纯、王璞命令队伍分头占领制高点,包抄敌军。战斗刚一打响,敌人便吓得屁滚尿流,慌忙逃窜,游击队跟踪追击。武胜县长张洪炳得知警察中队败退更是惊恐万状,一面命令关闭城门,一面向重庆告急,乞求援兵。
游击队并不打算攻打县城,而是向石盘乡大龙山开去,于28日与王屏藩部会师。
王屏藩原是石盘乡参议员,1948年初入党。8月28日早晨,王屏藩走到乡公所命令乡保武装八十人集合,到了石盘场学校操场,王屏藩跳上台阶,挥舞着拳头,郑重宣布:“我王屏藩反对,今天,我带大家上大龙山投奔,愿革命的跟我走,不愿的把枪放下,可以回家。”由于早已作好串联,都异口同声要求上山革命。与王璞、陈伯纯的四支队会师后,王璞任命王屏藩为三支队司令员,张伦任政委。
三、四支队合在一起由大龙山出发,30日宿营清溪乡黄花岭。次日拂晓,南充警察中队二百余人,清溪、石龙等几乡自卫队一百余人,南充李渡乡保丁,岳池、武胜的警察中队先后袭来。陈伯纯带领小分队有意边打边撤,将敌人引进埋伏圈,警察局局长林廷杰提着手枪,逼着士兵往前冲,黄花岭阵地上我方机枪、步枪一起开火,林廷杰被当场击毙。敌人溃不成军,游击队正待追击,突然武胜警察中队和乡丁民团三百余人赶来增援。王璞认为短时间不能解决战斗,时间拖长对我军不利,派三支队断后,掩护四支队转移。
9月2日,王璞带领先头部队,赶到岳池三元寨下与蔡衣渠、蒋可然领导的游击队汇合,并将合川、武胜、岳池三个县发动起义集中起来的四百多人合并为一个队伍,王璞任政委,陈伯纯任副政委兼司令员,王屏藩任副司令员,蔡衣渠任政治部主任。下设三个大队和一个突击队。不久,侦察员紧急报告说:重庆内二警、省保安团和南充、岳池、武胜、广安等县的警察中队、自卫队两千多人,从四面向我包抄过来。
王璞进行紧急部署,部队严阵以待。3日中午,战斗打响了,子弹向暴雨一样倾泻而来,敌人利用强大火力向我军发起猖狂进攻,我突击队待敌人冲到阵地前五十米左右才一齐开火,打得敌人狼狈逃窜。从3日—直打到4日晚上,打退了敌人十多次进攻,敌人死伤颇多,我方没有伤亡。
4日晚,敌人怕游击队夜袭,停止了射击。半夜,下起了小雨,天空漆黑,游击队趁机分兵两路实施转移。途中两队失去联络,张伦、陈自强队暂时分散隐蔽。
7日,王璞队押着在岳池秦家店子捉获的五名俘虏到岳池坪滩乡和武胜石盘乡交界的木瓜寨。木瓜寨四周均有石墙,后面是悬崖峭壁,左右是深沟,只是正面平坦宽阔,司令部将机枪等火力部署在寨墙不高的左方。
岳池县警察局局长魏仲枢和武胜县县长张洪炳分别带领警察中队、民团乡丁共五百多人,于下午三时分成四路尾追而来。
黄昏时,战斗进入紧张阶段。张洪炳等提着手枪押着乡丁往前冲,还欺骗乡丁说:“秦家店子被抓住的五个乡丁都被枪毙了,你们不往前冲被抓住是一样的下场。”王璞立即组织政工人员阵前喊话:“我们是的队伍,不杀害俘虏。”并当场将五个俘虏释放,揭穿了敌人的阴谋,乡丁们知道受骗,土气低落,战斗缓和下来。
天快黑时,王璞等开会商量对策,突然,正蹲在王璞左侧修枪的一个战士手枪“走火”,子弹射进王璞下腹,当场昏倒。大家立即组织抢救,因缺医少药,暂时用白药止住伤口,接着砍来竹子做了一副担架,准备突围连夜送到重庆。三次突围都被敌人密集的火力压了回来,王璞因失血过多,停止了呼吸。阵前失帅,战士们莫不悲痛万分。将王璞遗体藏在石崖下,部队撤离。第二天,敌人发现王璞遗体,残忍地一刀割下头颅,挂在石盘场一棵杨槐树上示众,后由附近农民就地掩埋。
王璞牺牲后不久,他的妻子员左绍英也被抓进渣滓洞监狱,已身怀六甲的左绍英忍受住了酷刑的折磨,拒不说出王璞的下落,并在狱中生下遗腹子“监狱之花”,1949年“11·27”大屠杀中,左绍英与刚满周岁的“监狱之花”一同殉难。
游击队员五十多人于9月7日深夜撤离木瓜寨,分散隐蔽。王屏藩到重庆后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后被派到下川东工作。陈伯纯化装成拉船的纤夫躲过敌人的层层封锁,搭船到了重庆,后又去铜梁找到川东临委委员肖泽宽,汇报了金子乡起义经过及王璞牺牲情况,由党组织派去川南继续战斗。刘石泉、秦耀在重庆被捕牺牲。
1948年7月,王璞派七工委委员杨奚勤来到渠县,向六工委传达联合起义的指示。六工委书记李家庆、委员熊阳、王敏召开会议,决定于中秋节(9月17日)在龙潭山发动起义,然后南下,与广安、岳池等地游击队会师。
原计划17日夜,范硕默化装潜入渠县警察局与地下党员督察长张天锡一道,以给警察局局长曾宗操“祝寿”为名,把几个警察队长灌醉,缴了敌人的枪,里应外合,迎接达县、三汇的起义队伍入城。不料这两支队伍未按时到达而使计划落空。
达县彭立人的队伍因敌人闻讯跟踪,好不容易才甩掉尾巴,到达龙潭已是20日上午了。
20日夜,各地参加起义的队伍到齐,进行重新编队,共编为三个中队,两个独立分队。龙潭中队二百多人,范硕默负责,临巴、土溪、卷洞合编为一个中队,一百多人,罗仁鉴、李建章负责,三汇中队一百多人,刘照钦、徐嗣镛负责,达县彭立人带领的三十多人及文星槽邵君儒带领的七十多人各编成独立分队。“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第六支队”司令员李家庆,政委范硕默,参谋长何尚,政治部主任任时雄。
当天夜里,大竹清河场“联防大队”一百多人,尾随三汇起义队伍上山来袭。司令部决定乘敌人立足未稳,主动出击。当即兵分三路,包围敌人。天将黎明时一声枪响,战士们的步枪、火药枪一齐怒吼,谁知狡猾的敌人早已转移到对面山上,这时,大竹保安团与重庆内二警、渠县警察中队也闻讯赶来,游击队反被包围。李家庆决定分路突围,转移下山。突然,滂沱大雨自天而降,正是突围的有利时机,大多数战士在熟悉道路的本地农民带领下从敌人包围间隙突围出来。
李家庆、范硕默转移到重庆,向上级汇报了龙潭起义受挫的情况。10月,熊阳化装潜入营山天池乡,向王敏及营山特支的传达了不再搞大规模武装起义,转入分散隐蔽的斗争的指示。但由于营山地下武装工作过于暴露,被敌人察觉,骆市、新店、天池等乡党组织先后遭破坏。1948年底,王敏被逮捕,关押于重庆渣滓洞,1949年11月14日牺牲于电台岚垭。
从1948年初奉大巫起义到8月下川东七县联合大起义,起义高潮过去了,川东地下党组织几乎都已经暴露,开展大规模的起义已不太可能。但斗争仍没有停止,原来的大队伍缩小成一些短小精干的武工队,在群众掩护下,仍继续战斗在华蓥山上,神出鬼没,偷袭敌人,主要有陈尧楷、徐相应等带领的大竹武工队,广安观阁、桂花场、邻水千丘磅一带由王群、向杰栋、胡正兴等领导的广(安)、邻(水)山区武工队,广安天池乡和邻水观音乡等地由张蜀俊、袁念之领导的武工队。
上下川东的武装起义大大地震摄了敌人,据上海《观察》1948年10月5卷9期“华蓥山之战”中说:
华蓥山的共军据闻在二万至三万人间,缺乏,但相当精良……两月来,华蓥山区共军已被击溃是事实。但这不是政府方面所向望的,他们要的是“聚歼”,而不是流窜。如今共军的流窜在安定的四川是一个威胁,在军力薄弱的四川也是一项严重的负担,所以地方政府于九月下旬又开始一个大的清剿,清剿山区以北如渠县等地起事响应的土匪。总指挥官员是专员雷清尘。……华蓥山之战一发生,四川地方政府与重庆绥署才着了慌,才认识了共军侵川的严重性,……既醒后的地方政府,现正尽力加强清剿及其他防御措施。……四川省政府计划中的扩充军队有两方面。一是正规军的扩充,计划增加保安队三至六团。一是组训地方武力,王陵基在各县民众组训副总队长训练班上称,将组训民众武力一千万人。重庆绥署也表示要请中央允准在川建军三师。于是,另一积极的工作,就是搜购军粮,除储备待用外,还要大量运出川,因之刺激米价大涨,还是苦了老百姓。
其实当时华蓥山的游击队不过两、三千人,报道中却认为有“二万至三万人”,可见游击队对敌人的打击是多么大,敌人调集了百倍于我的兵力围剿。
1948年12月30日重庆《新蜀报》报道“王陵基发表谈话:带回四项勇敢决策,川增六保安团治安无虞,清匪防匪剿匪当前要务”:
……关于本省自卫问题,本人曾面谒总统请求,已获面准,增列六保安团之编制与经费,连原有八团及已增编二团,本省将有十六个保安团之兵力……总统已允修理十万支步枪,发交使用,其余则尽量征用民枪,由各县县长、参会议长、副总队长,保证日后归还,如藏匿不报,则予没收充公……
至1949年5月,正当节节败退时,罗广文又纠集地方武装在华蓥山大搞梳篦清乡。挨家挨户清查户口,发给“身份证”,凡是无证件的,立即拘留审讯,实行“十户连坐法”,哪一户发现“奸党”,其余几户都以“知情不报”治罪。参加过广安观阁起义的郭兆银是广兴乡人,敌人勒令广兴乡保长梁惠光,甲长张前民交人,张前民交不出人被迫自杀,梁惠光只好假称郭兆银已自杀,叫郭的家属披麻戴孝,痛哭流涕,以图蒙混过去。不久,敌人发现郭兆银还活着,竟将梁惠光杀害。
罗广文部仅在广安清乡三个月,小小的广安县就有上千的人被关押拷打,被杀害的人没办法统计。仅桂花场就被枪杀28人,与桂花场隔邻的邻水千丘磅,几天内就枪毙了十九人。
敌人还在靠近山边的大小路遍布岗哨,对过往行人进行盘查,强迫住在山上的农民全部搬下山来,企图割断游击队与农民的联系。实行“踩山”,强迫当地农民手牵手走在前面,乡、保丁随后,罗广文部队牵着警犬督阵,对无法近身的刺丛和悬崖,就用机枪密集扫射,从山脚到山顶,实行“地毯式”搜索。
抓不到员游击队员,就把家属抓起来强迫交人。陈尧楷一家祖孙四代,徐永培、徐相应的亲属,江山霖的母亲、妻子等,被关在大竹,邻水的乡公所,日夜折磨,强迫他们交出自己的亲人。
6月25日,广安、邻水山区游击队长向道合等住在农民向杰明家,敌人前往搜捕,扑了个空,便将向道合怀孕的妻子舒万珍押到山上寻找,边走边喊,还用枪托打,折磨一天不见踪影,晚上又将舒万珍押到观阁镇公所吊打,舒惨叫连连,几次昏死。
让我们看看《四川省第十区保安司令部辖区清剿计划》中对华蓥山地区怎样实施围剿的:
(三)……本部即会同国军242师发动本区内大规模之清剿,即对全区施行严密封锁……
(四)清剿地区——大竹、梁山、垫江、长寿、邻水、广安、渠县七县,并以东山、中山、西山为清剿目标。
(4)乡、保、甲长得到部队入境通知,应将户籍册持往,协助严密清查户口,取具连保连坐切结;
(5)清剿期间,乡公会职员及警察、派出所应全体出动。组织民哨,指挥各保之侦探队,侦察匪情,报告清剿部队。
(1)各县县长、自卫副总队长、各乡镇长,大队附对清剿区内应详密设置民哨,冻结境内,使匪徒不致流窜,无法逃遁;
(2)清剿区内应予特别:昼间——应严密盘查行人,检查车辆,检查身份证,如有可疑之人,应立即扣留送清剿部队;夜间——应停止交通,断绝行人;
(3)凡民哨均应携带号筒、警梆或警锣,如发现匪类抑或逃逸时,应吹号筒鸣梆鸣锣,附近之居民同时鸣警传递。
(八)各县警察所、派出所、常备自卫队及联防队应就附图所规定之位置,一面封锁堵截,防匪流窜,一面就近搜剿。
(九)拟请国军两个团、保安二团一个营、第十保警大队三个中队为清剿主力部队,分别担任辖区内三山两槽之全面清剿任务。
(十七)凡匪入境,乡、保、甲人员及匪住地人民应飞报清剿部队或县府,知事而未报,经清剿部队查出,则以通匪窝匪论罪。
这是一份十分详尽、十分周密,散发着浓烈血腥味的屠杀计划,但是华蓥山人民顶着“通匪”的罪名,给游击队提供帮助,有些甚至献出了生命。
“双枪王”陈尧楷一直是敌人悬赏捉拿的要犯,1949年5月14日,陈尧楷等潜到“姊妹会”骨干张碧华家刚刚睡下,敌人就尾随而来。张碧华立即用身体堵住大门,叫陈尧楷赶紧由后门走,敌人撞开大门后,张碧华又将敌人死死扭住,为陈尧楷等赢得了时间。张碧华却被抓走,刑场上,她破口大骂,紧紧扭住敌人厮打,最后英勇牺牲。
学生出身的女员刘迦虎南大起义后掉了队,当地一位老大娘把她拉到屋里,给她穿上农家姑娘的衣服,脸上抹上一层泥,敌人追来时,老大娘说刘迦是她女儿,瞒过了敌人。
1948年5月,王敏与爱人周南若到营山发展组织,周南若即将分娩,因他夫妇俩都是外地人,没有社会职业作掩护,生孩子成了个难题,经民主人士李子麟掩护在营山卫生院秘密地生下了孩子。后来王敏夫妇都要下乡搞武装斗争,李子麟又想办法托了黄渡乡参议员王守怀收养了这一个孩子,王守怀还送了一支左轮枪给王敏作护身之用。
渠县龙潭起义后,周南若被捕关在营山县政府,周即对看守做策反工作,看守故意把牢门门扣弄松,周趁机逃出,跑到与李子麟相邻的彭家栈房躲起来,敌人发现周逃跑后全城,栈房老板十分害怕受牵连,李子麟就去给他做工作,叫他沉住气,三天后解严,李子麟又把自己的长衫、礼帽送给周南若,趁天黑将周女扮男装护送出城。
合川金子乡陈伯纯的统战对象王绍禾,在起义后曾被捕过三次,他其实对游击队的活动很了解,却没有暴露,后通过关系放出来,在重庆见到游击队转移过去的人,还递眼色叫不要与他打招呼。
1948年秋,广安观阁起义失利后,的母亲夏伯根、妹妹邓先芙、邓先蓉冒着极大风险将龙天翰、肖幼芳等十余位游击队员藏在家里一个多月,每天给他们煮饭、洗衣,后来,龙天翰提出要转移,邓先芙又叫人带路,将游击队的藏在稻草捆子里,越过敌人封锁线,顺利送到目的地。
1949年秋,年过六旬的农民冯永德因掩护赵唯而被捕,敌人把他押到乡公所,严刑拷打,以死威胁,冯老汉宁死不屈,穷凶极恶的敌人只好把他杀害了。牺牲前,冯老汉对前来探监的儿子、儿媳说:“我死而无怨,我死后,你赵叔(赵唯)他们的人来了,哪怕再没得吃的,也要给他们找吃的。你们这样做才是我的好儿子、好儿媳,一定要记住啊,不然我死也不安心。”他的儿子、儿媳潸然泪下,频频点头记住了父亲的遗嘱。
在川东地下党最困难的时期,一位从华蓥山转移出来的刚到重庆便发现已被人跟踪,危急之中,下意识地奔往自己心中最安全的红岩农场,躲过了一劫。
南方局虽然已经撤走,但红岩却在川东地下党员心中仍然是指路的明灯,外地来重庆的,没处落脚或遇到危急情况,仍会来到红岩要求给予帮助。
邓照明主动承担起清理组织和寻找上级组织的工作,并在思考中写下了总结,客观分析了形势,认为“领导干部策略思想上有左的倾向”
在1948年4月的破坏以后,川东临委已陆续离开重庆。重庆市、上川东、下川东干部受到重大损失。1948年8月,整个川东地下党组织,除了川南肖泽宽领导的一片外,原来的领导机关实际上都解体了,而重庆市、上下川东所属的保留下来的组织关系都由邓照明联系,此时邓照明也已失去了与上级的联系。邓照明、肖泽宽等在失去上级领导的情况下,立即主动清理组织,地下党的各级负责人也都积极地清理自己所属组织,寻找上级关系,并陆续与邓、肖取得联系。各地的组织、党员、进步群众都先后到重庆找关系。邓照明以重庆为中心开展活动,一批干部撤回到重庆,分散住在市内和进步群众家里。随后,又有一些通过种种关系纷纷找到邓照明接关系。
1948年9月,邓照明辗转去到上海,打算找钱瑛汇报川东遭受破坏的情况,邓照明并不知道,当时钱瑛已转移到香港,对于这一段曲折找党的经历,邓照明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川东地下斗争的简要回顾》中写道:
在王璞牺牲之前,我不考虑与上级联系问题,如今王璞牺牲了,我一定要考虑与上级联系向上级汇报工作,取得上级领导,才能解决川东党组织的工作问题。我当时只知道1947年秋临委成立时,王璞与在上海的上级组织钱瑛联系过,我就设法找钱瑛。我在川大时的同学赖卫民在钱瑛身边工作。驻重庆的贵州地下党员、老同学张又铭告诉我,通过蔡之诚能够找到赖卫民。于是1948年9月18日,我和蔡之诚一道去上海。这时在上海已找不到赖卫民,更找不到钱瑛。我写了一个报告交给上海市党组织,请转交给钱瑛,我等了一个多月,到十月底,报告原封未动的退回来了,并说上海党组织不管川东的事,不能处理,请我自便(意思要我离开上海)。我很失望,也很生气,把报告烧了,就回重庆。走的时候给上海党组织写了一封信,意思是说我到上海是找上级组织处理问题的,你们不帮助解决,我得不到上级领导的支持和指示,只能按自己的水平独立去工作。这种情况与当时时局有关,我到上海时正遇敌人枪毙王孝和,当时上海斗争也很紧张。刘国定、冉益智叛变后当了特务机关的上校和中校,他们带着特务到上海去抓钱瑛。我后来听说我党情报系统有个老(这时打入陈立夫的工矿银行工作)知道重庆地下党被破坏就给上海地下党打了电报。所以钱瑛及时转到香港。特务去抓她扑了空,我们去找上级也找不到。
11月,邓照明回到重庆,并到铜梁找到肖泽宽,就重庆市、上下川东、川南的工作交换了意见,总结了川东党组织遭受重大破坏的经验教训,统一了认识。认为在川东农村不宜再搞大的武装起义,在有条件的地方搞小型武工队,也不大量发展党员,注意保存和积蓄力量。邓照明还通过你自己在上海了解到的情况和对时局的分析,写了份约万余字的报告“团结人民,迎接胜利”,以作为特殊时期川东党政治上、策略上、工作上的指导意见,发往川东各地工委。最初,邓照明曾想:向各单位表明自己已与上级失去联系,大家如信任我,同意我的方法,就与我合作,接受我的领导,就一起干,不然,就各单位各个人可以自便。后来与肖泽宽商量后认为,如果这样会造成许多人精神上的不巩固,引起紊乱,便决定暂时不宣布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消息。肖泽宽提出由邓照明负责,自己协助,邓照明则觉得自身不是临委委员,自己的关系理应在临委领导下,提出由肖负责,自己协助肖,并保证一定服从组织纪律,两人相持不下,只得将意见保留下来,互相协作,开始了积极的工作。
在川东党积极寻找上级组织的过程中,上级组织也在通过种种关系寻找在川东坚持斗争的。12月底,城区特支负责人赵隆侃通知邓照明,立即到香港。邓照明到香港后向钱瑛汇报了情况,钱瑛指示:现在全国快解放了,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是“迎接解放,配合接管”,要防止敌人在垂死前的大破坏,应组织群众保护城市、工厂、学校等,加强统战工作。由于原川东临委只剩肖泽宽一人,决定成立川东特委,肖泽宽任书记,邓照明任副书记。川东地下党再一次建立了完整的组织系统。
邓照明在香港期间,用了好几天时间汇报了川东被破坏和目前的情况,并于1948年底和1949年1月,两次写了详细的书面材料,叙述了1948年以来川东地下党的情况,从每个方面分析了川东地下党遭受破坏的原因:
(1)在川东临委领导干部的(今年春天以前我自己的思想亦如此)策略思想上是过“左”的,简而言之,即“迅速开辟第二战场”的想法,策略思想非常贫乏简单,甚至能够说是直线式的。对川东敌人的政治、军事、特务方面的力量估计不足与轻视,对自己如何发动群众生长力量的困难又无深刻的认识,临委自身及各级干部如何加强群众观点,密切与群众联系,坚持群众路线的思想并未贯彻,便为自己规定下“解放本地区人民迅速开辟第二战场”的、当时还力不胜任的任务。于是下东奉大巫、云阳、南岸发动了武装起义;上东工委的大竹、达县、梁山地区实际在做的工作等于去建立公开的解放区,两处遭围剿,受到或大或小的损失。而特别关系重大的是重庆市,在左的策略思想影响下,太暴露,无警惕,误解攻心战术去一般地攻特务,市内采取统一的组织形式(一切是政治上的阵地战),致随时随地都有发生问题的可能。
(2)在今年春天,四月以前,这是川东党的很重要的时机,这时下东上东的武装斗争已转入山地,相当困难的在坚持,已撤出,转变斗争方式,然而对川东组织并非发生严重的影响,这时若临委的领导人员(王、涂、萧、刘)抓住这一时机,作彻底的策略上的检讨与转变,迷途知返,重新部署,还是来得及的(二、三月后在实际在做的工作中我们的策略思想已经有变化了)。但是这个重要时期错过了,致一个月后便发生了四月事件。
(3)四月刘国定的被捕与迅速彻底的叛变,应引起我党今后在白区工作(哪怕白区能继续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了)中更特别慎重选择,应特别注重品质,决不可只片面地看什么表面的才干。
(4)重庆市委出事是在四月初,下东老涂被捕是在六月中旬,上东广安出事是在六月底,即还有两个月或三个月的时间,尽可以从容地处理一切问题,然而竟未能处理好。四月份以后的善后处理工作未做或做得不太好。
(5)城市组织破坏影响到农村时,应采取适当的方式解决,并不是只有一条直路——武装起义。
(6)在武装起义发动以后,应在战争的指导上,切实掌握游击队的主动、积极与灵活,不然主力不能存在与发展;又应在主动、灵活的活动方式上找山地(平原与小丘陵地也可以,但颇不容易,需要更好的群众条件)与群众作依托,不然,必有部队被消灭或溃散、干部受损失的重大危险。反之,或大或小的根据地是能够创立的……
1、综观上东一工委这一段时期的工作,两三个月的武装斗争,把大竹山后区与梁达虎南区两个较有力量的隐蔽根据地打烂,另外的地方也受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刺激起敌人提高警觉来注意大巴山第一线与第二线的防备,本来这一带是很松弛的,结果弄得非常紧,使我们在这一带的工作发展深感不便,而所得的是:撤退出来,重要的有大批的干部未受损失(本地外地男女合起来近百人),保留了两支小部队与产生一批农村根据地的地方干部与军事干部,他们原来对农村武装斗争是完全生疏的,现已有初步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假若能虚心详细检讨,这中间有很重要的经验(我在斗争中与斗争后深刻体会到),若川东党的领导机构能够及时善于利用,是很有教益的。可惜老王并未充分重视与认识,致后来他自己直接领导的华蓥山区人民策略上重复着左的错误。我对这一斗争的看法,是所得不能抵偿所失的,但是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了不起的失败(因为我们并未受什么稍微重大的损失)。
2、左的迅速开辟第二战场的策略思想是错误的根源。“开辟第二战场”在革命战争的任务上是有必要的,但它应与川东党当时的实际可能相适应。不然,过低估计敌人的力量,与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在斗争中会碰钉子。自然,第二战场也是存在的与可能的,但,最初不是较大规模的游击队而是从小到大的,与群众切身利益相联系的小斗争。只要能从统治内部去削弱它,都应理解为第二战场。不宜作只有大部队活动,牵制它大量的兵力,才叫第二战场。
3、由于上一点的直接影响,使我们特别热心于醉心于建立部队的主力,虽然在我们自己的思想上与过去的工作经验中,明明知道必须由群众运动作起,由群众保卫或争取自身的迫切利益,才能健全的发展小武装斗争,再汇合与提高为大武装斗争;但是,我为当时山后虎南两个区域的现存力量所鼓舞,希望建立起主力,回转来用主力部队来开辟地区,扶助群众运动的发展,由群运的开展再可以加强主力部队与一般群众性的小武装斗争。同时对建立一支人民武装的主力部队的困难认识不足,对敌人会听到风声、等我军力量还未养成便调集大军来的可能性也认识不足。再次,对土匪的动摇性认识不足,被他们当时的好的表现(训练改编时表现却是好的),造成一种信任与乐观,花了不少的精力(其实这些精力应当转用在基础的农民群众工作上去)。现在归纳起来,土匪的特点是:“靠大不靠小,革面不革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今后基本的是搞农动与建立农民阶级性的武装;土匪部队一般也只能作为一部分不可靠的同盟军。
4、由于二、三两点的错误,便轻敌的实际在做的工作上的在建立公开的根据地,而不是去建立隐蔽的根据地,这便不能不引起敌人的围剿。
5、非常大的优势的敌人围剿到来时,正确地判断本区域已不能开辟成一个游击区,或必须脱离敌人才能保存自己时,及时撤退转移是完全正确的。这时转移的领导要坚决、灵活。不然,我们不仅不能保存这批干部与武装,恐怕又吃了彭庆邦在云阳竹叶坪所吃的亏了。——引申来说,老王他们以后在华蓥山,当不利时,未能坚决地绕过敌人上金城山去,是吃了不会转移撤退的亏。
6、军事干部、地方干部与领导人必须掌握主力的问题。军事干部各地方仍应注意提拔与培养,领导人应该掌握军事……。今后应特别留心培养教育本地干部,因为本地干部才能秘密的团结群众联系群众,若本地干部不动,妥协苟安,那么,武装斗争便难于发动,虎南区本地的妥协苟安思想大大地妨害武装斗争的开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无论情形如何,先总要把最重要的部分抓紧搞好,再去管其他的地方,以免失掉机会。
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去客观分析当时的情况。1948年川东地下党发生的这两起重大事件是相互关联、相互交织的。刘国定、冉益智的叛变是造成这一次重大损失的根本原因,但川东地下党在这一时期的政策也有许多值得总结的地方。受全国形势的影响,川东临委在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为自己定下了“解放本地区人民,迅速开辟第二战场”的任务,于是在下川东领导了奉大巫和云阳南岸的武装起义,上川东一工委又在大竹、达县、梁山地区建立了半公开的“解放区”,党员干部都比较暴露,一旦敌人围剿,目标明确,力量悬殊,游击队很快处于劣势。而在同时,重庆市区的组织错误地理解了对敌“攻心战术”的意图,缺乏警惕性,采取了将《挺进报》直接寄给党政军头目这一过激的作法,导致了敌人恼羞成怒,最终将《挺进报》破坏。刘、冉被捕后叛变,迅速祸及整个川东。从4月刘、冉叛变到涂孝文、骆安靖叛变,这中间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若此时能果断处理好市区的善后及隐蔽,是能减小农村组织的破坏,道路也并非只有武装起义一条。这一时期,川东地下党遭受的打击是极其惨重的,川东地下党在上、下川东地区长期经营的一批党的“据点”和“两面政权”,以及游击根据地基本丢失,川东临委所属地区除川南两个地工委和上下川东少数几个县,以及重庆市内个别组织外,大都遭到破坏。受损失最严重的是干部,共损失临委级干部四人,地委级干部四人,工委级干部十五人,还有区级干部及普通党员数百人。
由于川东地方党组织的惨重损失,干部严重不足,中央对重庆和川东解放后的干部配备问题作了慎重考虑。1949年7月,在南京拟定了陈锡联、谢富治、阎红彦、张霖之、曹荻秋、魏思文等川东区党委和重庆市的党政军主要领导成员;11月8日在湖南常德配备了地、专和区县各级主要干部。干部的来源则主要由华东局和西南服务团组成,华东局调来809人,川干队254人,主要由学生组成的西南服务团849人,而川东地下党只有81人;其他的还有由二野三兵团和二野后勤系统抽调的专业方面技术干部194人。(待续)